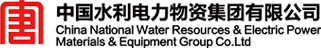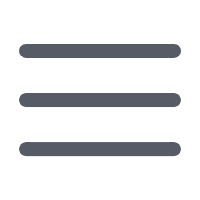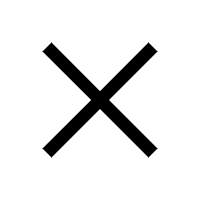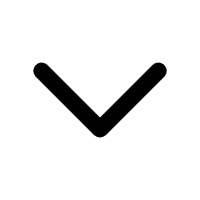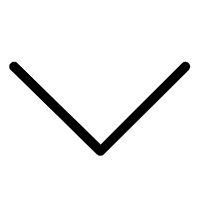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批热血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千里迢迢来到了大西北沉寂的沙漠,这其中就有我的爷爷奶奶。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认真讲讲爷爷的故事,抚平他漫长的近九十个年头或悲或喜的冗长岁月。
我的爷爷于2020年1月永远地离开了我,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他病危让我赶来见最后一面的情景。当时的我忽然觉得站也站不稳了,忧伤侵袭过来,一股脑地撞击着我的胸膛。当我匆匆赶到嘉峪关时,爷爷已经在监护室里,全身插满了管子,紧闭着双眼,只有耳边监视器传来的滴滴声和他并不匀称的呼吸告诉我——他还在,最终爷爷还是没有扛过死神的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火化之前,我的手在大衣兜里不停地搓磨着他生前一直佩戴的手表,一种无形的生命气息仍旧在这些熟悉的物件之间游移,只能感觉却无法触摸。最后把手表放入墓地的那一刻,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放声痛哭的同时我很想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是什么。可是,他无法再告诉我了,只有他的生平故事告诉我他奋斗的一生和作为核一代人的骄傲。
爷爷出生于1930年,河北泊头人。1963年,响应国家号召,带着我年幼的爸爸和叔叔们拖家带口的举家搬迁到地处大西北戈壁滩的核工业404厂,那里是当时我国核工业重要生产基地,为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发奠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初厂址选址的地方环境极为恶劣,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株树,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二三十里地以外只有茫茫戈壁。那里的年降水量当时是50多毫米,很多过去的内地人,到了那里才真正体会到水的重要。刮大风的时候,向前走路要弯着腰,脸朝着地面,否则就走不动。自然条件虽然艰苦,但对从事放射性工业生产来讲,却是比较理想的环境。就是那样一个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外界眼中的保密基地,在1964年生产出第一个高浓铀正式核部件,通过不断的技术攻关,保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相隔两年零八个月,于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地爆炸了氢弹。当时厂区的荒凉,我小的时候就听爷爷不止一次地絮叨过,不过在我上学时那个小城的福利区、厂区和马路两侧种植的大批杨树、柳树,已经陆续长大,两侧的防风林带也已形成,与外界相对独立的小城里有动物园、商店、医院、学校、公安局等等基础设施,只有从老人口中能依稀听到建厂初期时的艰难,尽管不能感同身受,但是作为一个核三代的骄傲在小小的我心中已然扎根。
伴随着我日渐长大,爷爷也早已退休了。1996年这个代号404,几乎全封闭的半军事化小城暂停相关核试验,但依旧保持着高度的秩序化,2004年404厂嘉峪关生活基地奠基,也标志着小城整体搬迁和二次转型的开始,404厂成为利用核能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后处理基地。彼此相互熟稔的人们离开了那座小城,但是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收入逐年增高,大家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而爷爷那一辈老人也都陆续离开了他们钟爱的核事业和这片热土。
不管你是否相信,过去就是那样;不管你能否面对,过去就在那里。爷爷那一辈人的一生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反右斗争、三年经济困难、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等近现代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的人生起起伏伏,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一生正好见证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他们的命运遭际是那一代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命运。
爷爷去世了,就像一本摊开的书合上了,但我对他的经历一直铭记在心。我有时想,爷爷他们这一代人过得很不容易,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会动荡和剧变中度过,经受了很多磨难。但我对他们那一辈人的了解又是零星的、不连贯的,只能通过他们的只言片语和他们晚年的安静祥和去感受。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既湮没了许多本该留下来的东西,又创造着许多以后可能会消失的东西。宇宙永恒,人生苦短,我们所能见证的,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更多的东西,只能穿越历史的时空,在遗迹和流传下来的文字中去寻找、去体味。
写下这段文字时,我知道,爷爷,他一定读到了我的思念。时间在流逝,却总有一种记忆会缓慢地沉淀下来,藏在心灵深处,空明并且奇异,不可企及,却总是遥望不止。